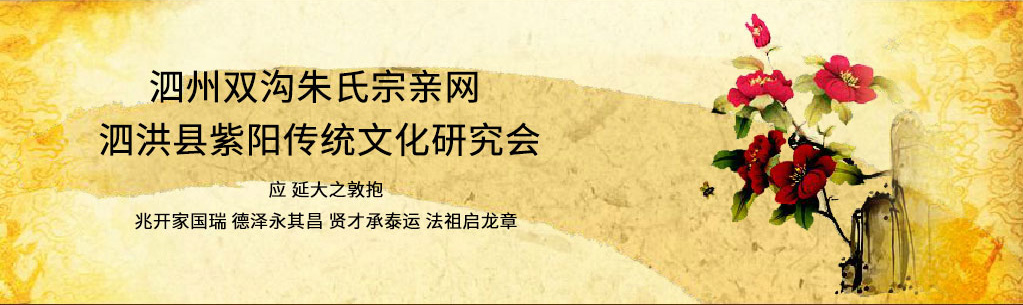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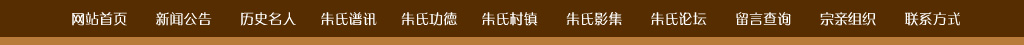
| 父亲和他的战友 --杨如平 |
| 发布日期:2013-07-23 12:31:50 点击次数:3206 |
我的父亲杨维振曾是新四军十一旅32团二营的抗日战士,每每回忆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忆那些生死相依的战友,老人家总是激动不已,甚至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把父亲那些难忘的经历记录下来,是父亲也是我的夙愿。 两淮保卫战中蒙冤的翟宝三 翟宝三曾在抗日名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当兵,后经周折参加了新四军。他不仅参加过抗日战争,还参加过解放永城、血战泗县、保卫淮阴等战斗,是位战功显赫的军人。他在华野战九纵队当营长时,我的父亲是他的通讯员。 华野战第九纵队,是由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整编而成,司令员是张震,编制五个团兵员。1946年8月,九纵配合山野八师围攻泗县国民党新七军172旅时,损失较大,75团张永远团长阵亡,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英雄团长,后来被就安葬于泗洪烈士陵园。 据父亲回忆:打泗县我们团主要是配合山野八师进攻东门,半夜发起进攻时下起暴雨,我随连部涉过没膝深的护城河,拥堵在城下的开阔地,攻城突击队爆破器材很多失效,因为雨大路滑,进攻的机动性和增援都受到很多限制,突击队没打开缺口,部队暴露在开阔地一带,进退两难。上级下命令一定要在天亮前打开缺口。守城的172旅老兵多枪法准,战斗意志也很顽强,突击队伤亡很大,进攻收效甚微。我跟随在指导员李兴智副连长史文德旁,在暴雨中焦急等待冲锋的命令。天快亮了,如果还不能攻进城我们都会变成守军的靶子。拂晓却接到撤退命令,我们在泥泞地边滑边倒撤到护城河边,没想到河水已暴涨过胸口,有的战士一不小心便被洪水卷走,天空微晨,守军开始向我们射击,我第一次见识曳光弹,就象身边的道道闪电感觉无处藏身。我奋力渡过护城河,刚到岸边天已大亮,完全暴露在守军的枪口下,曳光弹一闪便带来一片弹着点,泥水飞溅。我不敢上岸,幸好岸边有一丛杂草便趴在水里一动不动。河边时而漂过尸体,成群的蚊虫蚂蟥在身边盘旋。我泡在水里整整一天。天黑后我才悄悄爬上岸归队。当晚又参加进攻八里桥171旅的战斗,张团长不幸阵亡。 九月,部队来不急休整,便仓促投入“两淮保卫战”。翟宝三营长率领二营六连(副连长史文德),在泗阳众兴——石工头阻击战中浴血奋战,顽强抵抗蒋整编74师和新七军的强悍进攻。 父亲记得很清楚, 翟宝三在《忆八天八夜阻击战》中记叙:我们这个团是 中午12时,敌又以重炮向我轰击,步兵再次向我冲来,又再次被我打下去。敌人正面数次进攻遭到失败后,改变了进攻路线,少数兵力仍摆出向我正面进攻的架子,约有两营的兵力由张庄绕道张家地(庄稼地),顺河堤从六连左翼猛扑过来,猝不及防,六连部分阵地被敌占领。情况危急,六连长史文德说:“营长, 怎么办?” 我说:“还能怎么办,反击夺回阵地!”同时,我命司号员吹反冲锋号,重机枪掩护六连反击!六连接到反击命令,全连官兵端起步枪,向敌群冲过去。冲在最前面的是一排长徐永明,他一连刺倒五六个敌人,最后在众多敌人围攻下壮烈牺牲。 十七日从石工头撤下来后,二营由开始的200来人只集合了40几人,我父亲杨维振就是其中之一。据台湾战史载:“张灵甫46年9月16号向蒋报捷:言已攻下淮阴。但17日仍与敌9纵激战整日于石工头,遭到敌9纵一个连的疯狂逆袭、反击”。这个连就是二营六连。 战后,因在石工头阻击中没有坚持到天黑,翟宝三营长被代理团长卸了枪关了禁闭。翟宝三认为“虽未坚持到天黑,但基本上起到了阻击的作用。这次战斗,本应客观地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但团的个别领导却不听我的如实汇报,粗暴地对我指责、谩骂,并指责我曾经提他的意见了,不如实向纵队反映情况,说我先撤退了,并把我送到纵队去,拿我是问,要求对我严肃处理。这哪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翟营长一气之下,跑了。他没有跑回家也没有跑到蒋军队伍里去,而是跑到地方部队继续革命。 1956年审干,“不实之词”把这位战斗勇敢有个性的营长压的身心疲惫。好在还有点文化,会写会回忆会思考,找老战友老首长,坚持上访申述。,1982年终于“落实政策”,其实就是还历史本来面目。今年五月,这位勇敢可敬又充满智慧的老人离开了人世,终年93岁。 也许有人会说,朝前看吧,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好,这种说法太轻描淡写混淆是非,什么是政治环境,在这个政治环境下掩盖了多少历史真相多少人的心酸血泪?国共内战,许多年青士兵今天被俘解放,明天又弃暗投明,这一仗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另一仗又生死相博。在国军作战勇敢,为共军也奋力拼杀,跟随哪个队伍哪个党派,这种责任不应该由普通的年青人或军人来承担。内战就是一个民族的伤痛。翟宝三老人历经千辛,坚持历史事实坚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遭后人误解的烈士宋延年 宋延年(江苏邳州人)和翟宝三是战友也是朋友,抗日末期宋是二营营长翟是二营副营长。我父亲回忆:1945年5月,在陈集围点打援时,营长指挥二营埋伏在路边麦田里,突然袭击来增援陈集的一个伪军营,大获全胜,二营一个营以很小的伤亡代价消灭伪军两个营。45年8月,在攻下日伪占据的永城县时,父亲搜挖出伪团长窦峨家中一箱银元一箱手枪,营长奖励两丈布六块银元。二营被授予“雪枫营”。营长为宋延年。 宋延年十四岁时,家人劝其考农业学校,受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他立志报考军校,当时八路军宣传工作做得好,就去了延安,入抗大学习。身经百战,历任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1947年7月,在山东临朐围攻李弥整编第八师的战斗中,刚由参谋长提升为副团长(时九纵75团改为华东野战军二纵五师14团)的宋延年,率领突击营近七个连冲入西门城区,不幸的是,冲入小校场开阔地,四面全是蒋军火力,后续部队遭封堵,几百战士(具体人数待考)或亡或俘或降,全部损失。宋延年阵亡,时年24岁。李弥整编第八师防守城西的是308团主力(团长曾元三,其三营防守朐山)。南麻临朐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不忍回顾的败仗,二纵(司令韦国清)首次打攻坚,面对胡链李弥的梅花子母堡没有更有效的爆破手段,加上暴雨天气,导致人海对火海,战后五师缩编为两个团。 据有关史料记载:粟裕手中4个纵队。 1950年21军颁发烈属证,据宋的侄子宋双平叙述“大伯父牺牲后,部队来俩战士接我奶奶,说去部队开会。到部队后我奶奶得知大伯父牺牲的消息,顿时晕了过去,奶奶听顶替我大伯父职务的那位副团长说,大伯父是在指挥部队作战时被炸死的。” 然而,时隔六十多年,一位名叫伯玉的网民在网上发贴说:14团7个连余部200多人在临朐城内集体投降。我认为“集体投降”一说非常不严谨不恰当,容易造成不战而降的感觉,不符合事实。这种说法让宋家后人和老战友无法接受。宋氏兄弟正努力寻找战场幸存者,希望用历史事实驳倒伯玉说法。我也劝父亲好好回想一下,搜索点具体史料来证明宋延年烈士,以宽慰老首长后人的悬念之心。父亲说,当时部队上下就一个说法,宋副团长阵亡牺牲了,部队打了败仗撤退缩编,再也没听说突击营的音讯,宋副团长和战士勇敢冲入李弥防线,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及后人的怀念和敬佩! 宋氏兄弟在网上发现了我父亲的回忆,我们就有了直接的交流和讨论。宋氏兄弟说,一直想去山东临朐战场,实地考证一下,详细了解研究临朐的战斗经过,用更加具体的事实让谣言站不住脚,研究战争就是为了避免战争。为维护前辈的荣誉维护烈士的尊严,宋氏兄弟尽心竭力不懈努力。这不仅仅是宋延年烈士后人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参加过那场战役幸存战士的责任。 回顾探究前辈的历史,并不是炫耀荣誉,也不是揭露对手的反动,而是站在民族的角度审视内战,纪念每一位阵亡的军人和不幸遇难的平民,给后人展示更加完整清晰的历史画面。民族同胞相互残杀的悲剧不能重演,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今天歌颂明天打倒的混乱政治环境也应该结束。 言传身教的指导员李兴智 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李兴智(河南沂源人)指导员,1945年7月,李兴智介绍父亲秘密加入共产党,并派父亲去团部学习,准备回来当文化教员,就是拉拉号子唱唱歌。父亲五音不全,一首最简单的歌练半天也找不到调,但对识字写字很感兴趣,指导员说,你当不了文化教员(副连待遇),就帮我管管文件当文书(排级待遇)吧。刚当文书时,父亲不会写战斗总结,一时半会也教不会,指导员干脆列个格式,时间地点敌部队番号本连负伤人数阵亡人数,敌伤亡人数缴获枪支数量等,填数据就行,真管用。李指导员有文化也有带兵水平,空闲时父亲就向他请教,这个字怎么写那个字怎么念,国共两党有什么不同等等,受他的影响,父亲也学会写点日记。平时指导员的大小事父亲也会抢着干。 1945年10月,连队分配一套掷弹筒,那时叫小钢炮,各班排都不要嫌重,指导员说杨维振你就负责背吧。炮架带六发炮弹,行军打仗累得够呛。在攻打伪军占据的曹村站时,父亲抓住机会一口气将炮弹全放光,战斗结束全连无一伤亡,指导员说炮弹放得好,敌人吓蒙了。46年9月退守淮阴时,张灵甫74师特务连骗开城门突入城区,父亲睡着了,李指导员慌乱撤退中摔一跤,正巧倒在父亲身边,一把拽起他:杨维振,还不跑,想当俘虏啊!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懂交朋友,津贴花不完(文书每月一斤肉津贴),李兴智有时急用就会喊:杨维振,借点钱。一九四八年初又安排父亲去蔡桥教导团学习。有一次,一个刚解放的小战士犯了纪律,指导员气得抡起皮带就抽打,年青时的李兴智脾气比较暴躁,但对父亲还是关爱有加。1953年21军入朝前夕,父亲和指导员有机会在南京见了一面,父亲用最后一块袁大头请老战友下馆子吃了一餐。 今年春节期间父亲思念老首长,打电话到其西安家中,董阿姨接的电话,说:病重了,听不到看不到也不会说话了。也是今年五月,李兴智老人离开人世,终年89岁。我一直想有机会去西安,一定代表父亲去看望李兴智老人,现在终成遗憾。 郭楼保卫战中的通讯员任国凤 小时侯,邻居小伙伴家常有大人的老战友来串门,偶尔听到点战争年代的小故事,我很是羡目。曾问过父亲:你的战友怎么不来看你啊?父亲不耐烦:哪有多少战友,能活下几个! 1944年12月下旬,父亲和同庄几个青年来到二十几里外的芦庄报名参军,部队的番号响亮: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45年元月3日发军服发枪,父亲印象深刻就把这一天定为入伍时间。二月在祖楼集参加第一次战斗袭击日伪抢粮队,同乡二虎中弹身亡。八月在解放永城战斗中,突击队有几个老乡率先跳下城墙被敌俘虏,解救后溜回家不干了。49年初打到长江边上,同时间入伍的三个老乡(其中一位机枪连副连长),悄悄约父亲一起开小差,怕过长江想回家种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父亲还帮他们出具证明,当地政府给了点津贴补助。从46年7月到48年底,父亲所在连队大量补充兵源有五六次之多,父亲知道的营团以上军职伤亡七人(张永远,屈树义,秦贤安,宋延年,程坤源,董营长,佘琦义),逼迫离队一人(翟宝三),连职伤亡十多人。但有一位战友父亲不会忘记,就是通讯员任国凤。 1948年8月,父亲调二纵五师十四团三营八连任副指导员。12月中旬,正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进入关健时刻。杜聿明率二十多万人马聚堵在永城以北陈官庄一线,试图继续南下与南边被围的黄维兵团会合,打破野战军围堵,扭转战场被动局面。离陈官庄杜聿明指挥部只有四华里的郭楼,成了两军争夺的焦点。14团奉命参加保卫郭楼的战斗,要用人体把郭楼铸成铁楼。天寒地冻万马嘶鸣,在中原这片哺育他们成长的富饶土地上,簇拥着近百万相互仇视的军人,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要展开空前撕杀。 父亲回忆:13日夜,营部下命令,要八连组织突击队驱逐消灭阵地前沿修筑冲击工事的敌军。连部决定组织突击排,带队连干按副指导员连长指导员副连长顺序执行。我二话没说,来到前沿察看地形,月光下视线还好,要冲锋的开阔地二百来米,地势较平坦,估计不到一分钟可冲到对面。我做好冲锋前的准备,第一突击排已在战壕里列队待命,我问排长都准备好没有,排长说准备好了。我深呼一口气:跟上我,不许掉队!第一个翻出战壕,弓身向对面快速冲去。刚跑出几十米敌军开始射击,机枪冲锋枪子弹乱飞,中弹的倒下没中弹的继续冲锋,我不下令突击队战士就不会停止。接着迫击炮弹落下,一发,两发——,突击队落入火力网,队形散乱,我刚想喊不要乱跑,亮光一闪“轰”的一声,刹时头重脚轻控制不了身体,直立着不能动。这时有人在后面拉我一把,将我按倒地下。过一会儿我缓过一口气清醒了点。 “指导员,你受伤了”听得出是通讯员任国凤的声音,他正捂住我额头上伤口,我焦急问排里的人呢?他说还好。敌军还在射击,任国凤不管三七二十一,背起我冒着枪弹左闪右躲,终于撤回战壕。第二突击排已整装待命,连长手一挥“上”,战士像波浪一样翻出战壕向黑暗中扑去。敌军又开始射击,开阔地上炮火闪闪,烟土飞扬,这次敌军射击更激烈更准确。不一会儿,黑暗中有人叫喊:“连长不行了连长不行了”,几个战士七手八脚把连长拖进战壕,这位平时爱训人的连长已停止呼吸。连续两次突击失利,连里气氛有点沉闷焦躁,虽然看不清人的表情,但都有同样的感受。指导员的第三突击队进入出发阵地,年青的面孔,乌黑的钢枪,月光下像一座座雕塑,指导员阵前动员:大家手脚利落点队形散开些,跟我上!又是一阵波浪翻出,紧接着是激烈的枪炮声。陆陆续续有战士撤回战壕,焦急喊着:指导员的腿炸没了。八连三次突击伤亡六七十人,最后,副连长带领幸存战士一直打到淮海战役结束,还俘虏一千多蒋军。 我和指导员被护送到师部野战医院,医院设在张瓦房,一路上多亏任国凤的细心照料。在医院疗伤期间我试着给家里写封信,内战爆发后一直没和家里联系,没想到几天后大哥用小车推着母亲来到医院,杨楼离张瓦房一百五六十华里他们一天赶到。母亲心里很难过,说家里人传你被打死了,劝我离开部队回家养伤。我安慰母亲说,放心死不了,等解放全中国我一定带您去南京总统府逛一逛。一句不经意的话,母亲等盼了四年,1952年我被选派到南京解放军政治师范学校学习,终于接来母亲,实现了这个愿望。 在整理父亲回忆的过程中,我感叹不已,那不是一般意义的战争,就是相互间的残酷绞杀。泗县攻击战,泗阳众兴保卫淮阴阻击战,宿北战役的来龙庵阻击战,山东南麻临朐战役,莱阳战役水沟头阻击战,淮海战役郭楼保卫战等,仗仗都是我死你也死,一个连一个营甚至一个团拼下来只能集合几十人。我惊奇的是父亲竟然能亲历一劫又一劫,生存到最后。我对内战史不太感兴趣,但通过父亲的回忆,我初步了解了作战勇敢的翟宝三营长,言传身教的李兴智指导员,年青有才的宋延年烈士,刚烈英勇的佘琦义团长等。前辈的历史令我追思与崇敬,我赞叹他们的勇敢和执着,赞叹他们在艰难环境生死战场上的无畏气概,但是,更让我震撼和追思的是那些死去的有名无名先烈以及成千上万连自已也不知道会变成敌人的年青士兵。他们长眠地下,将年青的生命奉献给未知的世界。江山不是皇帝的,也不是哪个党派团体的,江山属于在这块土地上世代繁衍劳作的生灵大众,夺取江山就是夺取民族的生命和自由。 |
泗州双沟朱氏宗亲网 泗洪县紫阳传统文化研究会
苏ICP备08006391号 制作维护:扬州宏瑞科技